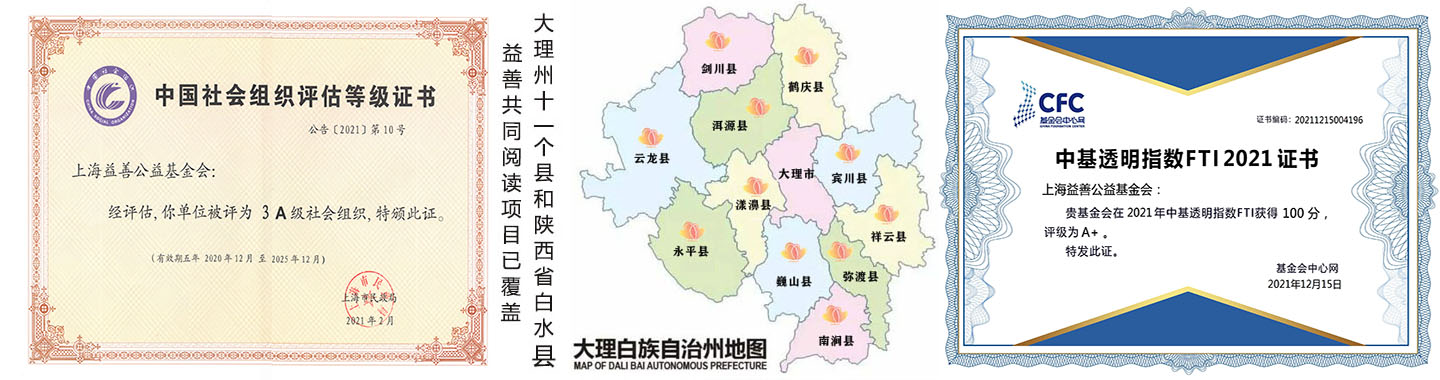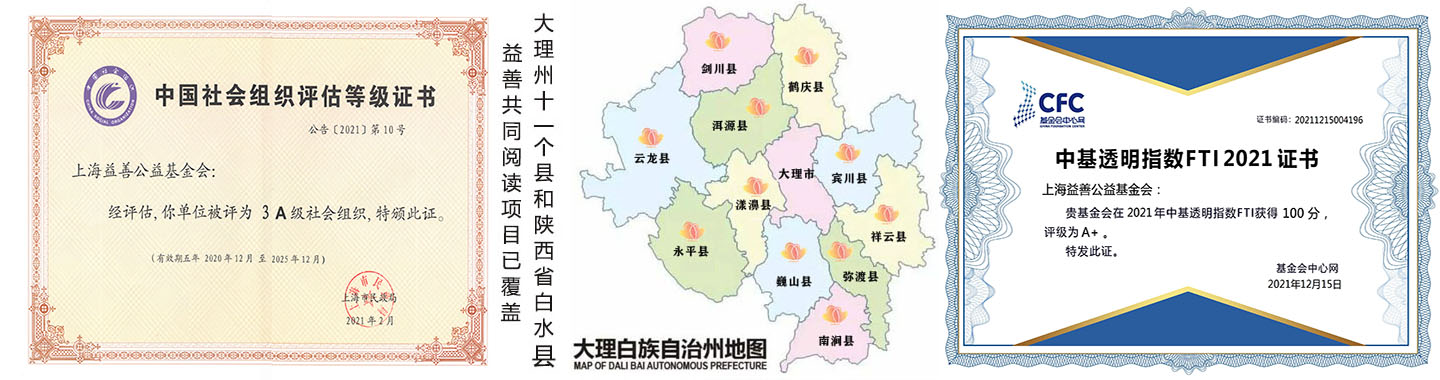-----关于“大理·虹”助学计划来由的完全报告
李同新
(一)
关于助学,缘起于一个偶然。
2013年5月,小白,杨四,曹斌,昌山和我,应乐文之邀在西安欢聚。尽管毕业后联络不断,但几个兄弟如此天南海北聚拢过来,还是难得。
西安期间,乐文尽显地主之谊,我们游山玩水、对酒高歌,忆同窗往事,说人生经历,甚是酣畅。一日席间,乐文说起大学里的一段往事。一次,他到系里领汇款单,金额是12块5毛8分。老师很奇怪地问他,为什么家中会寄这点钱?她哪里知道,这就是乐文妈妈能寄给孩子的全部费用。
这个细节,让众人唏嘘不已,也一时陷入沉默。20多年,我们从恣意的青春走到了人到中年,成家、立业,无论是生活还是工作,人生还是事业,早已今非昔比。很多人与事已经随风而逝,不再回头,但总有一些东西不能割舍、无法丢弃,就像我们不可能改变20多年前睡在上下铺兄弟一样的命运与缘份,也无法忘记,我们曾从哪里出发,有过怎样的起点。
返程前往咸阳机场的路上,曹斌忍不住问起乐文:现在陕西的贫困家庭是啥状况?乐文答:一个架子车就能拉走全家的家当!又问:那我们能不能帮助下贫困人家的孩子呢?再答:可以。需要帮的人真不少。
这简短的一问一答,让我们顿生助学之念,也开始热烈讨论。
为什么不呢?今天的我们,谈不上多少功成名就,也并非亿万富翁,但是,当年一个“十二元五毛八分”就可以让乐文走出家乡、走向未来,今天一个穷苦孩子一年的学费也不过是推杯换盏时喝掉的那瓶西凤酒,改变一个孩子以及他的家庭的命运原来可以如此简单,并不需要我们放弃打着“飞的”欢聚的快乐,不需要我们改变享受生活的品质。我们为什么不能帮帮那些“当年的自己”?
对于助学,我们实在不陌生。很多人都以不同方式、不同程度地参与过这一最为传统的善举。而此时,我们共同的想法是:如果要做,就让它成为我们同学人生的一个共同纽带,成为一齐向青春致敬的一个特殊仪式。
(二)
西安,成了“下一站”的启程。
惜别时,击掌盟约:去乐文的家乡,去那个“十二元五毛八分”的寄出地,看看我们能为20年后的“乐文”们做些什么。
6月8日,乐文、曹斌和我,分别从西安、上海、厦门出发,再度相聚乐文家乡湖北麻城。
这一次旅程,开始与地方、学校进行了初步接触,也让我们的助学想法,从最初的简单、感性、激情,化作更多细致、理性与思考。那个原本只是不成型的朦胧想法,一点点清晰。
坦率说,在今天,以兄弟、同学、朋友之力,集资一笔钱,捐建学校,资助学生,完全可以表达我们的心意。也是最常见的方式。但这真的就是我们此刻想做的吗?且不说今天的助学公益机构存有那么多的质疑,也不论这其中有多少事本该由政府担负,单就切身体会而言,求学时代的我们,既需要那笔雪中送碳的钱,但又绝不仅仅是。
能够让已过不惑之年的我们萌生亲力亲为助学的起因又是什么?不正是我们在重新找回同窗情、致敬青春路的时候,再回首同学故事,希望向同学致敬吗?助学,某种意义上说,何尝不是以另一种方式资助年轻的我们?
我们想做的,我们要做的,不仅仅是助学、助他,而是延续我们的青春回忆,助己,助人生。
很多人一次次问着相同的、很实际的问题:你们会拿出多少钱来助学?你们会投入多少精力做此事?你们究竟想做到多大程度?
其实,这也是我们最初不断问自己的问题。
我们的确告别了贫困,甚至走向富裕,但远未到可以随便捐出大笔资金投入公益慈善的地步;我们有心公益,希望介入,但还必须为自己的事业去打拼、去经营,远未达到可以全身心投入的程度;我们想要助学,希望成全他人的人生,但并不意味着我们有勇气牺牲自己乃至家人的生活品质。相反,我们希望的是,不求多么轰轰烈烈,不求任何世俗功名,只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帮助他人,成全自己,提升快乐。不在乎规模是大是小,哪怕只是让几个仍在靠家里全部的“十二元五八毛分”寻找未来的寒门子弟减一点压,帮助他们扫清一点不公平的障碍,让他们看到希望、放下沉重,这就是我们的成功。这也才是我们想做的。
也因此,我们认定:做此事,绝不为任何功名谋。既不能把这件事变成一场几个人的“善心大发秀”,活在别人的感恩与掌声里;也不想把这事件弄成“虎头蛇尾”,既愧对同学,又有负养育我们的家乡父老的期盼。当然,更不想“大撒把”后,成为某些地方官僚为之利用的政绩资本,甚或挪用款项。
湖北之行,没有想象中顺利,但正是与地方、教育机构的沟通中,让我们对此次的助学计划有了深入思考,有了较为明确的方向感。一是寻找与我们自身有关的助学对象,带着一份感情和责任去做,让它成为我们的精神出发点与落脚点。二是希望能够尽可能地参与,把简单地助学变成长期的联系,那是青春期学生需要的,也是我们可以从中继续充实人生的。三是拒绝功利心,拒绝名利场,拒绝形式主义,只想脚踏实地,真正让孩子受益。
这一想法小范围地透露给了一些同学,得到了很多认可、支持。特别是,对资助对象锁定与同学相关的这一出发点,极为认同。不少同学当即表示“算我一个”。大家广开思路,提出了更多的建议,有的提议关注自闭儿童,有的呼吁艾兹病患者这这一特殊群体……对集资方式、运作机制等,也积极建言献策。这让我们备受鼓舞,也坚定了做好做实的信心。
不过,想到最早刺激我们萌生此心的那个“十二元五毛八分”,我们还是决定,从原点出发,此次行动锁定在同学家乡贫困孩子的求学上。
秉持着这个理念,我们开始寻找、探路、落地。
(三)
8713的同学来自五湖四海,全国大部分省区都有。我们首先把目光投向了那些中西部贫困地区,那些与我们班同学有关的地方。同时,从各个渠道,我们也在积极了解与公益助学相关的政策,借鉴经验,做好前期准备。
当湖北麻城的考察还在进行中,我们同时与峥嵘学籍地云南大理、吴焰学籍地贵州凯里的当地教育部门初步接洽。
前期联系的结果,既喜且忧。每个地方都表达了“欢迎”的热情,但与我们希望直接参与的方式又有一些距离。几轮往复,初步感觉,峥嵘所在的大理,各方面条件比较匹配我们的初衷,可行性最高。
大理,洱源。峥嵘的家乡。26年前,峥嵘从洱海之源走出,在洱源一中、下关一中读完初中、高中,然后一路向东,来到长江入海口的大上海;又带着四年复旦情怀,在1991年回到故里。20多年过去,当年的白族少年如今已经成为大理州文化局局长,把个人的爱好、志向与他热爱的故乡紧紧相连。
在峥嵘的穿针引线下,我们与大理白族自治州教育局、大理州洱源县教育局、大理下关一中、洱源第一中学等,进行了积极有效的沟通,有了助学合作的初步意向。
一个设想要落地,需要实干。
(四)
从上海到昆明,空中距离1965公里。从昆明到大理,公路距离495公里。从大理到洱源,73公里。
7月23日,曹斌和我飞抵大理,开始了启航之旅。
3天里,我们分别与大理州教育局学生资助管理中心负责人、下关一中张副校长等人进行了详细沟通,了解当地学生的实际困难、教师的客观诉求;我们走访了峥嵘的母校下关一中、洱源一中,深感师恩难忘、师恩难报;我们驱车来到三营乡、炼铁乡等乡村教学点,听了7所乡村完小的校长老师们诉说着他们的坚守与清贫;我们还来到了峥嵘老家的白米村寨子,在这里,既对同窗四年的同学有了更深入的了解,也感受着这片土地上的朴实与醇厚。
第一次在曲曲弯弯的盘山公路上辗转数个小时终于头晕目眩;第一次看到除了黑板和粉笔便无任何教学工具的教学点;第一次知道一所学校可以只有1位老师和19位学生;第一次听说这样一个真实的对话-----当学生问老师“人坐飞机,是坐在飞机的哪一部分”,老师的回答是“我想,是坐在翅膀上吧”……
对我们来说,西部,农村,从未这么真切地呈现在我们眼前。与其说是走进大理,不如说,我们是在走近大理,走近同学,走近我们的梦想。
就经济状况和发展水平来说,大理,洱源,在中西部地区并不算太差。洱源一中、下关一中,也都是超过2000名学生的规模较大的中学。不过,也因如此,这里并不属于公众视野里的“贫困学校”,社会各界对云南贫困地区的各类捐赠不少,但两所学校并不在急需关注的重点之列。
然而,洱源中学的学生大多来自贫困边远山区,家境并不是太好;下关一中虽是全省排名前五的名校,学生中仍有许多寒门子弟。这些学子,反而成了容易被“忽略”的群体。目前学生受助主要来自国家助学金,覆盖面为30%,一等为每年2000元,二等为每年1000元,尚未有成建制有系统的社会捐助。
当峥嵘带着我们一起回到他的母校,表达想为学弟学妹们做点什么时,老师们露出的那种笑容,让我们真切地感受到他们内心的欣慰和骄傲。的确,老师们教书育人不求回报,然而,学生的惦记与回望,无疑是对他们最好的回报与致敬。
他们的眼神让我们领悟到,也许,我们依然要为素昧平生的地震灾区人们伸出热情的双手,还会向毫不知名的连一顿简单午餐都成为奢侈的山村孩子投去关切视线,甚至,我们也可以为素不相识的怪病男孩捐一笔医疗费用,然而,那些就在我们身边,或者说与我们有某种特殊联系的人们,是不是更有责任与情感去关注呢?
那样的资助,不仅仅是捐赠,恐怕多了一点义务。不仅仅是公益,还多了一点责任。不仅仅是单纯的助人,还多了一点助己的真实。
(五)
大理三日,还让我们对此前陌生的中国乡村教育、农村教师,有了新的认识,使我们的助学行动,增加了新的内容。
与洱源县三营乡、炼铁乡等中心学校、完小的校长老师们座谈、实地走访了一些偏僻的教学点后,展现在我们眼前的,是这样一幅有些沉重的“中国乡村教育图”。
农村留守儿童的教育成长是一个极大的社会隐忧。当地农村空心化现象严重,往往只有老人、妇女和儿童“6138”部队。小学里的留守儿童比例已经高达90%。这些孩子的父母在外打工,经济条件相对过得去,但多为与爷爷奶奶相互依存,缺乏亲情呵护、缺乏家庭约束,再加上外界的一些不良干扰,撒谎、打架、不想念书,成为这些孩子身上普遍存在的性格特征。而查找资料后更发现,留守儿童不仅成为受伤害最大的一个群体,也成为青少年犯罪率最高的一个群体。
面对这一群体的未来,老师们深感忧虑,又觉无力无助。我们的心情也格外沉重。这些孩子渐渐长大,会像他们的父辈一样涌入城市,也成为未来城市的主人翁。所以,这些孩子将成为怎样一种人,拥有怎样的精神世界,他们对社会持有怎样的看法,哪里是什么家庭问题、农村问题、中西部问题,跟身处于大城市、就算是在国内国外穿梭的每个人,难道没有关系吗?我们既不希望自家孩子的同学里有马加爵,更不希望乘坐地铁、高铁、飞机,走在超市、商场、广场时,遭遇各种猝不及防的暴戾与伤害。
留守儿童的教育成长,如何解决呢?当地老师也坦言,从根本上解决不外乎两个办法,一是当地有足够的就业机会,让他们的父母回来;二是跟随父母去城里上学。可是目前看来,这两条路都不太现实,也不知何时才能实现。或许,最为现实可行的,就是通过乡村老师、农村教育这个重要环节,让教育真正成为“实现社会公正的伟大工具”。
然而,目前肩负起对这群孩子直接“教化”的乡村教师,处境同样令人揪心。
当一位校长心酸地说起学生的家境时,有多少人知道,其实当地代课老师这一群体的生活更为窘迫,每个月只有600元的工资,即使转为合同制,工资也不过1100元;
当年过半百的老师慨叹,有了社会的帮助可以让孩子打开视野,有多少人知道,当地很多老师,几十年里最远去的地方,仅仅是县城洱源,很多课本用文字呈现了城市生活、现代设施,但乡村的师生们完全无从想像;
当老师谈及留守儿童的孤独性格,希望乡村里能走进一些音乐、美术、心理等专业老师,又有多少人知道,直到现在,洱源的一些乡村小学教学点,大多只有1-2个老师,守护着一二十个学生。他们何尝不是一种孤独的“留守”?他们的“孤独”,又有谁来解救?
当政府、公益机构、企业为改善教学师资给当地配备了一些电脑,又有谁知道,许多电脑根本成了“摆设”,只是因为当地没有网络,没有相关培训。
……
今天,“北上广”的召唤,“人往高处走”的心态,那些受过教育的、年轻的老师选择了“走出去”,至今坚守乡村的老师们,大多已经年过半百。很多人批评他们知识单一、年龄老化、理念落后,这些可能确实不假,然而,也恰恰是他们,才肩起了农村教育文化的火种。也恰恰是他们,在过去的几十年里,把无数的“峥嵘”们带出山里,送入城市,成为国家社会栋梁;现在,一片“清退”声中,留守在农村延续着这火种的,依然还是“卑微”的他们。
一位同学由此感叹:城镇化后,许多农村面层着产业空心化、人员老龄化、基层空洞化的困境,乡村文化更岌岌可危。曾经以乡村学校的存在形式,深埋于中国乡野的文化种子,正有被渐次抽离、掏空的危险。对遥远的乡村来说,每一个学校,是一堆火;每一个老师,是一盏灯,那光虽是暗淡,却明明灭灭地闪了几千年,是烛照中国乡村的一线微芒,让人温暖且踏实。他们是令我们仰望的人。有灯在,中国的希望才在。
大理之行,也让我们更加坚定最初的行动。中国要解决的问题实在太多太多,无论是寒门子弟的求学,还是乡村教育的拯救,这是一个多么宏大、系统且长远的问题,凭我们这小小的力量,不可能做到,我们也没有那么大的志向去担负一个本应由国家之力去做的事情。然而,在力所能及的范围里,在我们步入了一个感恩年纪,是不是也可以为老师、为学弟学妹们去做一点点努力、争取一点点改变呢?哪怕只是让那些寒门子弟看到一种希望,让乡村教师感受一种温暖,也许就能少一个马加爵,多一个王峥嵘?
我们甚至有了更长远的想法:农村教育是一个挑战性的问题,我们是否可以全班之力,以洱源为基地,尝试逐步改变贫困乡村的教育现状。走访现场期间,我们已经感受到了从教育局党委书记到教学点老师的渴盼与支持。或许,我们改变不了很多,但相信,只要我们去做,一定能改变点什么。我们不奢望我们的助学计划作出什么惊天动地的大事,但如果我们能在洱源取得一点可以让别的集体借鉴的事,或许已经是一个了不起的成就!
(六)
20多年前,在复旦校园,我们爱唱苏芮的歌“是我们改变了世界,还是世界改变了我们”。我们无力改变世界,我们甚至都无法改变这大的环境,但是,我们也相信,有一些改变,是我们可以做到的。而且,在这样的改变中,我们自己也获得人生的快乐。
结束了洱源考察,从崎岖的盘山公路返回大理的路上,天空中突然升腾起了一道彩虹,在蓝天里格外显眼。彩虹,是历经风雨的见证,也是美好愿望的祝福。在这个彩云之南的地方,我们也望见了心中的彩虹……